




作者:張慧蓀

在夢境和黎明的交界處 – 從〈蕁麻〉談女性現實生活中的妥協與慾望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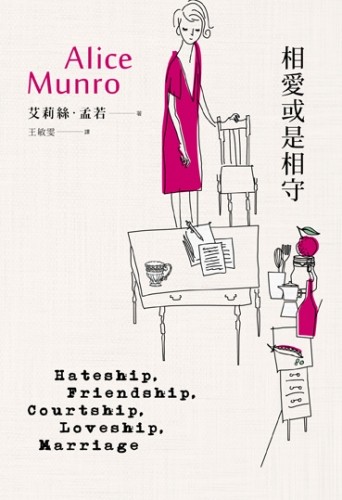 那是一個女人成長過程中生命的記憶,雖然短暫,卻又那麼強烈而深刻。
那是一個女人成長過程中生命的記憶,雖然短暫,卻又那麼強烈而深刻。
它發生在記憶之中,卻存藏在歲月之外的時空。
像是一個夢境,既遙遠、迷離卻又那麼真實。
留下的,是如同在『夢境和黎明的交界處』,那隱隱的天光,若隱若現的晨星,似真似幻,空留迷惘及失落,卻又深具啟發性。
一開始,書中的女主角就以第一人稱,回顧她與小時玩伴麥克的相遇。
「1979年夏天,我走進朋友孫妮在安大略省俄克斯橋鎮附近的屋子,看見一名男子站在料理檯旁,做番茄醬三明治。」
***
幾十年後兩人意外而短暫的相遇,童年相處時的默契仍自然的存在他們之間,引領著他們看見彼此。然後,高爾夫球場幾乎奪命的暴風雨,成了鮮明的記憶。之後,他們再度分離,如同童年時不預期的分離,差別的是,這一次,他們都是經歷過人生底谷的成人,像是成長必然要付出的代價,再度的分離,像是人生的必然,沒有不捨的對話,沒有正式的道別,也沒有沒有留下隻字片語。像是人生的必然。
後來,女主角再婚, 她與第二任先生去找過那房子,但始終沒找到過。
但她找到了高爾夫球場。
麥克,再度在她的生命中消失,但在她心裡面,卻留下如穹谷般的回響。
當我看完整個故事,再回頭看到這段開頭,心理面有著深深的震撼及撞擊。
似乎故事的開頭,才是故事的結束。
消失的房子,消失的人物,如同消失的夢境。
但它卻真實存在過,存在記憶當中一個單獨拉出來的特別的時空,記憶可以是遙遠的,這獨特時空中的歲月卻是凝結的。
儘管這些人事物不再出現,但那曾經的存在,卻咀嚼了一個人內心深層的孤單,托住了一個人真實生活中需要吞嚥的悲喜,幫彼此的生命延伸出一個可以存在記憶深處的棲息港灣。
這一切,或許正是來自它的消失。
***
他們的相遇,是在女主角小時候住的農莊。麥克跟他父親是游牧式的鑿井人。
他比她大一歲,他們相遇時,他九歲,她八歲。那時是暑假。
他們玩在一塊兒,馬廄、穀倉、長毛狗『森林警衛』、屋旁的楓樹、河流、石橋都有他們的足跡。女孩兒總是跟著男孩,好像這麼理所當然。
有一次,他們離開了農莊,走到石橋那兒。那邊有很多男孩子,他們是麥克上的鎮上學校的男孩。
『跟妳的那個是誰 ? 』『誰都不是,只是她。』
麥克很容易就加入了那群男孩,帶著她一起。他們玩的是戰爭遊戲。男生出去打仗,女生在裡面準備彈藥。受傷的男生,可以叫一個女生的名字,這樣,這女生可以盡快把傷兵拖去所謂的醫院敷傷。
她幫麥克做武器,而麥克叫的是她的名字。她只為麥克一人服務。
在那麼多聲音中她得一直保持警覺,當那喊聲來時,像是一條電線麻過全身,有種瘋狂效忠的感覺。
那天在回家的路上,他們平躺在河水裡,想要弄掉身上一身的泥巴。
回到家的時候,家裡的一位臨時工,取笑他們在泥巴裡打過滾。 他說 : 『等你知道就得結婚了。』
母親責備了那位臨時工說的話,她說他們是像哥哥和妹妹一樣。
其實,女孩心裡覺得,她媽媽說錯了,他們不像哥哥和妹妹,也不像她所知道的夫妻,因為夫妻住在各自的世界裡,簡直認不出彼此來。
他們像穩定熟捻的情人,之間的連結不需要多少外在的表達。對於女孩,那是很嚴肅很憾人的。
在她對麥克的感覺裡,每當在他面前,那既模糊而又讓人感到羞恥的情慾化成了四射的興奮和溫柔,她暗自崇拜著麥克,內心充滿虔敬的願意接受任何麥克分派給她的角色。他們之間不需要解釋或排定的角色,女孩知道她將會輔助他、敬仰他,而男孩將會指引她和隨時保護她。她每天早晨渴望見到他,渴望聽見那鑿井人的卡車碰碰撞撞一路開來的心情中醒來。
午餐時,老麥克和小麥克都是和他們一起吃。小麥克和她從不說話,也不太看對方。女孩的父親和老麥克談話,老麥克每一番話都以笑聲結束,那笑聲裡有點寂寞的回響,好像他還在井裡。
有天早晨,那卡車沒來。午餐桌邊少了兩把椅子。工作已經結束了,他們再也沒有來的理由了。
女孩沒有意識到當麥克在那最後的下午爬上卡車, 一走就永遠走了。沒有再見,沒有揮手。為什麼她還沒理解到多少事就要結束了 ? 許多事從此畫下句點。她懷疑是不是大人特意計畫的不要小題大作,以免她變得太難過和難纏 ?
但最初的震驚過後,她沒讓任何人看穿她的內心。包括那臨時工每次見到她就取笑 : 『妳男朋友丟下妳跑掉啦 ?』
她知道麥克一定會走得。只是她完全不知道,要一直等到麥克不見了以後,才知道缺席的真正含意。她自己的領土是怎麼全盤變了,好像山崩過,席捲了所有的意義。
幾星期後的有一天,是秋天,女孩和母親去鞋店,母親在試穿鞋,女孩在鞋店門口等。她聽到一名女人喊 : 『麥克』。
她忽然相信這名她不認識的女人必定是麥克的母親。他們一定是有甚麼事回鎮上來了。她急忙跑出去 --她相信再過一分鐘就可以見到麥克了。
眼前,她看見一個女人揪住一個大約五歲大的男孩。他正拿一個蘋果在啃著,那是雜貨店放在門口人行通道上的一簍蘋果。
她停了下來,不可置信地瞪著這小孩 -- 一個普通的名字,一個扁臉生了一頭骯髒金髮的小孩,好像一場荒唐、不公平的魔法正在她眼前演出。女孩的心大力猛跳,好像她的胸部正要發出哀嚎來。
我們時常,不是年紀太小,小到不知道如何表達那個失落,就是年紀太大,大到知道聚散離合,就是人生的常理。我們表面上的平靜,其實是瞞不過自己的內心。直到遇到一些事,在一些場景,我們才會知道我們多在乎。
***
她和麥克的再度相遇,是在她的女性朋友孫妮的家裡。
她和孫妮是在溫哥華認識的朋友,兩人懷孕期剛好錯開,因此一套孕婦裝輪著穿。在溫哥華,她們時常喝著濃咖啡,抽著香菸大肆聊天,聊彼此的婚姻、夫妻之間的爭吵、她們各自的缺點、有趣又不大光明的動機、遺忘了的野心。她們同時讀榮格,並試圖追蹤她們的夢想。
照理說在人生那段時期,女人忙著生育,正是最混亂的時候,心智都被乳汁淹沒,但這兩個女人依舊興致勃勃地討論著西蒙•波娃、T.S. 艾略特的<雞尾酒會>。
而她們的男人完全是另外一種心境,每次跟他們聊這些,他們會說 : 『喲 ! 就是文學嘛 ! 妳好像在教哲學概論。』
這是年輕女人,難得的快樂時光。大膽、勇敢,帶點心高氣傲的囂張。但真實的婚姻生活,總是逐漸消磨了這一切。丈夫、孩子、忙不完的家事,取代了過去的快樂逍遙。婚姻中靈性的枯竭,也讓女人安靜沉寂了下來。
甚至孤單,讓人變得敏感而脆弱,顯得患得患失。
***
她離開了婚姻,留下了丈夫、房子、所有婚姻裡累積的東西,期望能過一個遠離虛偽、遭受剝奪或羞恥的生活。她知道走出婚姻牢房的旅程漫長但是必須。
但對兩個女兒的思念,是她無法忍受的痛楚。
她開始一個人的生活,決定以寫作為生。一想到完全不必做家務,就讓她快活無比。但她也開始注意到,每天早上隔著窗戶,坐在人行道上桌子旁的那些人; 對他們來說,這種生活一點也不值得稱羨,只不過是孤單人生糟透了的習慣而已。
在她住的後院,時常有人開狂歡派對。有時夜幕低垂,後院的狂歡派對又開始,音樂聲夾雜著叫喊及挑釁,她反而會感到恐懼,那是一種自己不存在的感覺。
她也有『交往的男人』。有時,他們的見面,讓她『心蕩神迷又安心』。但男人離開後,她的眼淚往往不由自主地流下來, 滿心不安像石頭一樣沉重。因為她從男人那裏覺察到了甚麼陰影或違和感,或是甚麼無心的舉動,像是從男人那裏隱隱傳達給她的一項警告。
她正學著讓一個男人自由,也讓她自己自由。
這恐怕是許多人在婚姻中做出選擇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- 面對婚姻中的枯竭、沉寂,或是出走後面對排山倒海而來,足以淹沒自己的孤單、寂寞。
孤寂,是一個人靈魂的底蘊,時常跳出來喧鬧不休,提醒我們它的存在。直到我們學會在生命中安置它一個恰當的位置,接受它正是自我的一部分,生命的一部分,孤寂,才會恰如其分地在未來人生一個又一個的故事中,扮演它該有的角色。
***
在孫妮家裡的廚房,她遇見了正在麵包上抹番茄醬的麥克。
麥克,理短的頭髮,深陷的淺色眼睛,瘦削臉,舉止輕盈,脾氣好但嚴肅。是種習慣性的,但不討人厭的矜持。
他們很自然就認出彼此,並衝向對方,幾乎同聲說 : 『是你』。
他們一起邊洗碗邊分享童年發生的事,麥克記得的事和女孩記得的不一樣。
但也有兩人都記得的事項,像是泥巴砲彈,和打仗遊戲。
他們也談他們彼此的家庭。
那天晚上,她被分配到前一晚麥克睡過的床上,那一整夜裡她睡不安穩,在夢裡,那床聞起來像水草、河泥和熱太陽下的蘆葦。那是童年熟悉的氣味。
她睡得很淺,做的夢充滿了性的慾念,但卻障礙重重。
有時,她醒來,發現自己像是擱淺在一塊乾地上。她知道麥克不會來找她,麥克是個謹慎的人,他會自制。
有時清醒的時候,她也懷疑自己對這男人了解多少 ? 對方又知道自己多少 ? 他喜歡聽甚麼音樂 ? 他對女人有甚麼期望 ?
畢竟他們曾經的相遇,只是童年的一段記憶。這記憶被釘在過去諸多交錯留戀的情結中。包括隔著時空的、既遙遠又清晰的童年往事。包括兩小無猜的默契、彼此的支持及安全感。這一切,相對於當前真實的人生,過去那一去不復返的單純、年輕的歲月,顯得特別珍貴而令人懷念。 而麥克,正是代表著過往的這一切,對女人來說,他是一個充滿意義的符號。
***
雖然天氣預報會下雨,他們一起去打高爾夫球。麥克說我們碰運氣。
她喜歡他說『我們』,這好像又回到童年時他喜歡她跟著他,一起去冒險。
開車去球場的路上,她坐在他的旁邊,在太太位裡,這讓她有種少女暈眩的欣喜,開始幻想成為一名妻子,彷彿她從來沒當過。她自問,是否真的已經找到值得相守的真愛,擺脫過去格格不入的自己,變得快樂起來 ?
但真的單獨在一起了,他們反而有些不自在。
她問起他太太的家鄉,問起他的小孩。她也說她自己已分手的婚姻。她突然有種衝動想要告訴他生
活裡的悲傷和需求,以及她內心的矛盾。她說 : 『我想我的小孩。』
可是麥克沒有說話。沒有安慰、同情或鼓勵。
她是不打高爾夫球的,但如同孩提時代,他要她跟著他。
他說 : 『一樣,你可以來替我背球袋。』
其實,她不真的需要背球袋,她只是跟著他、看他,甚至不必看他。
球場沒有人。
麥克偶爾開口說話,她知道未必是對她說,她不需要回答,其實也無法回答。
那像是兩人在一起生活久了,心靈契合、情感親密,便能夠理解的默契。
她做的,也認為應該做的,只是給麥克一個放大了、擴張了的自我意念。一種讓他安心的感覺,像是周圍有人托住他的孤獨的篤定感。
她知道這是已有了相當交情的女人才能給出這種讓對方滿足的期待。
前一晚夜裡強烈痛苦的肉慾,在這過程都淨化裁剪成一朵朵勻淨的母火,細心守護,如同妻子那樣。
時空相隔了幾十年,當他們有機會單獨相處了,但那樣的相處,既熟悉、又陌生。熟悉的是過去的相處模式及默契。她信賴著他,他保護著她。
陌生的也正是那種熟悉及彼此了解的默契,但他們從卻從來沒有說出來的。如今,單獨相處卻無法迴避的那份情感,讓人感到陌生不安。
童年的那段關係,如今看來是超越夫妻、超越情人的關係。它似乎被凍結、區隔在現實的人生,保持著它的純潔、美好及放心,對如今他們面對的疲憊而滄桑的真實人生,那份關係格外的顯出它的意義,令人珍惜。
***
他們沒有打完這一局。 一滴雨開始匯聚成的狂風暴雨,幾乎可以奪去他們的性命。一大片天空脫開了似的朝他們壓下來,厚重狂暴的風雨打在他們身上。他們無法站直,一到空地上,馬上被風雨打倒。
麥克始終握住她的手臂,面對著她,以他的身體抵擋著風雨,但那簡直像一枝牙籤般起不了作用。他正對她的臉大叫說了甚麼,可是她聽不見。他握住她的雙臂,往下移到她的手腕,然後緊緊抓住,把她往下拉,讓她離地很近蹲著,近到他們無法看到對方,只能看到腳邊已經破開土地的細小河流。
麥克放開了他的手腕,箝住她的肩,仍然,他的接觸依然帶著克制,不那麼自然。。
他們維持這樣,直到風勢過了。
雨仍在下,只是轉成普通大雨。
他們顫顫站起來,幾乎沒有力氣。他們試著微笑,然後短促的親吻,用力地擁抱了一下,像是劫後餘生的儀式,不是身體的想望,而是認識到倖存下來了。
在走向停車場的時候,太陽活力四射的光線曬在他們身上,女人站著不動,深深的呼吸。『有件事我沒跟妳說。』這突然的、沉沉的聲音,嚇了女人一跳。
麥克告訴了她關於他最小兒子的事。他最小的兒子三歲,去年夏天死於他倒車時的意外事故。
她的腦海掠過事發的那一刻的那些畫面。孩子的母親從屋裡跑出來的那一刻。
但她跟在他的後面,甚麼都沒說 – 連一句善意的、無濟於事的空洞安慰都沒有..他們已超出那以外了。
他是個跌到過谷底的人,人生的谷底是甚麼樣子。他和妻子兩個都知道,這事把他們倆綁在一起,這種事若非拆散人,便是讓人緊緊相繫,一輩子。他們共同承擔這件事的真相,在兩人之間的位置,冷而空虛,上了鎖的。他們搬了家,在家裡也幾乎不提那孩子的名字。他們搬家後的人裡,沒有人知道這件事。連他們共同的朋友,孫妮和她老公都不知道這件事。
一個沒有說出口、不再回顧的痛,在歲月的累積之下,它會成為甚麼面貌 ?在麥克的家人之間,那是一個公開卻沒人揭開的秘密,它只是被凍結,永遠不會消失。沒有經過面對傷痛及哀悼的歷程,傷口不會痊癒,它只是隱藏在家中每一個人的內心深處,繼續散發著它的冰冷,以疏離的關係形式,繼續它的影響力。
***
她是個知道的人,卻不屬於他們搬家後碰到的人。
他和她共享著那份悲傷的秘密,但她不是他的妻子,不是他的情人,也不是像孫妮他老公那樣的朋友,她是他自己的、一個知道的人。一個存在於他的真實人生之外,既親密又萍水相逢的人。
***
他們沒有再見面了,她從沒再問過孫妮他的消息,或得到任何他的消息。
雖然多年後,她和她的第二任丈夫再度尋訪過遇見麥克的孫妮的住處,但一切卻都消失了,只找到了高爾夫球場。
如果竟而再見面了,也會是一樣。知道自己地位的愛情,不冒任何危險卻像一條甜蜜的涓涓細流,依舊生機勃勃,一座地下的泉源。
它像是愛情,時常來到心靈深處叩門,觸動心弦。但它又超越愛情,知所進退,過濾掉了情慾,卻有著不用說出口的默契。那個默契,有著天真的放心,儘管時空相隔,當他們再度重逢,那種不需言語的默契,仍舊在他們的心裡面定位著彼此的關係,超越愛情、友情、超越時空歲月,在他們各自的人生,托住彼此面對人生滄桑時的孤寂,可以有一點點安慰,知道,遠方有這麼一個人,他懂得 !
問題與討論
1、從女孩到女人,故事中的那些部份可以觸動妳的心,為什麼 ?
2、他們之間的關係,是愛情嗎 ? 你如何詮釋這種關係 ? 這種關係會影響彼此個別的婚姻關係嗎?
3、對於家人共同經歷的傷痛,麥克的家人是如何面對 ? 這會是一個好的面對方式嗎 ? 你個人的看法又是如何 ?


















